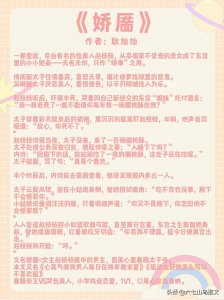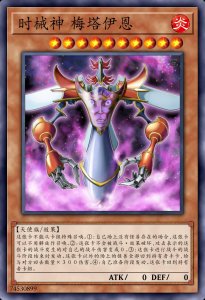中国封建社会的迷局之“逆淘汰定律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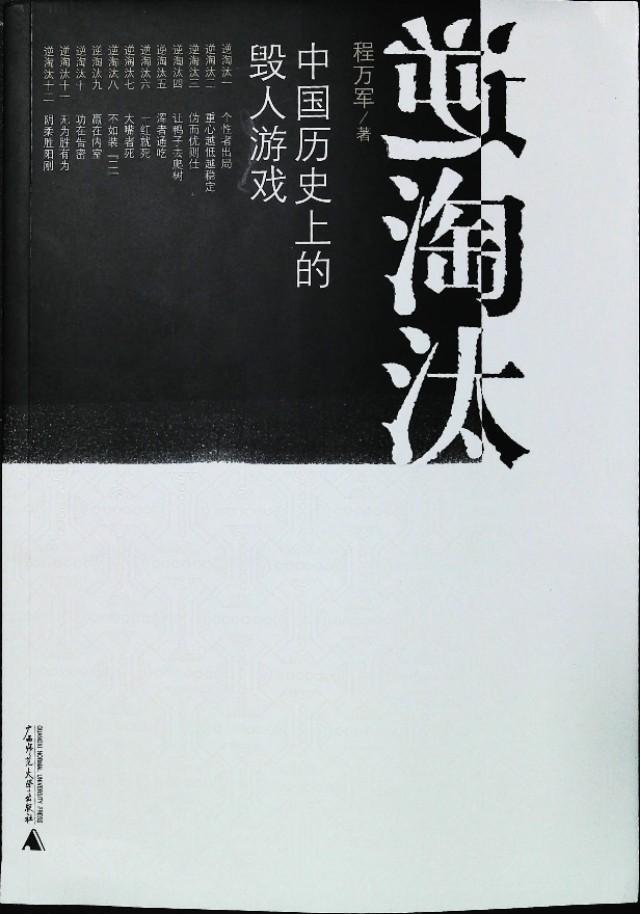
何谓“逆淘汰”
何谓逆淘汰?一言以蔽之,曰:劣胜优汰。
这是与达尔文《物种起源》唱反调的“退化竞争”,却在人类的局部历史舞台上经常上映。
人才出局,草包过关,“劣胜优汰”历史剧在东方神州断断续续播映了两千多年。对于过关的草包,那是美不胜收的人生喜剧;对于被废的人才,则为彻头彻尾的毁人游戏。
毁人游戏中常见——奇才败在庸才手里;有文化的人败在没文化的人手里;讲人格的人败在不讲人格的人手里;说真话的人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,这是不折不扣的逆淘汰。这种现象的背后,是一口口埋葬人才的陷阱,一出出光怪陆离的用人迷局。
毁人游戏虽然荒唐,却据有独一无二的生存空间。在中国固化的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格局下,从政经到文化,政府垄断一切社会资源,人才除了依附政府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。在封建时代,当官是唯一的发达通道,走仕途几乎形成了全民共识,所以人人都想当官,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飞黄腾达捞个一官半职。然而当大家挤作一团时,那种情况也有如食腐动物麋集在腐尸上一样。竞争不仅残酷绝伦,而且是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。悲喜交加的逆淘汰注定要在这样的非正常竞争下发生。

中国的封建历史太长了,所以毁人游戏总是能与时俱进、自动升级换代。
当非正常竞争的逆淘汰占据了时代“主旋律”,人才之被毁,则成为挥之不去的痛。浩瀚的二十四史,冷眼看来,不啻“毁”人不倦的仕途陷阱。尔虞我诈,刺刀见红,无止无休.…千古悠悠,有多少人才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地填进了这口巨大的陷阱中,直至在井中发霉变臭?
臭水井中,是寄生物的天堂。奴才的命运好于人才,庸才的前途胜过奇才。井底发出的是逆淘汰的哨声,余音惊悚,千年不绝。
惊悚的哨音里隐含着暗道音符。那里包藏历朝统治者的用人术和肉食者的生存暗道,以及逆淘汰游戏的N种规则,也是中国人才的N种命运。
发生于“争上游”路上的逆淘汰,其前提是:你是不是人才,领导说了算。然而,领导是不是伯乐,谁说了算?历史的空谷里,无人应声。
或许当代“过来人”会告诉年轻人:“你是不是人才”与“领导会不会用你”,有时完全是两码事。诚然,历史往往会回放,验证“过来人”说的没错。

不过,历史也许没有细分,这世上有伯乐,也有伪伯乐,说不上你遇到的是哪一个。用你还是毁你,伯乐明循“优胜劣汰”,伪伯乐则反其道,暗循“劣胜优汰”——出于一己之利,他们喜欢让猴子去游泳,让鸭子去爬树。
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,就是重演历史。历史一再令我们发出“惜哉人才”的长叹,漫漫仕途,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人才?制度毁他,上司毁他,同僚之间的相毁更加严重。中国历史上,名臣良将都有过相似的被同僚“下绊”的遭遇,“掣肘”现象频频作怪。一个人才出现后,一万个庸人等着毁灭他,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瞬间扼杀,淹没于茫茫人海——这似乎成了一道无解的千古难题。
一个专注于潜规则研究的民族是无望的,诚如一个成天琢磨“卡位”抢官的人才,久而久之,也必定被废,退化为八面玲珑的庸才。然而,我们不得不承认,在封建时代,任何想走仕途的人皆要过“暗道”这一关。无论德才兼备之人,还是二者全无之辈,要想不被淘汰,只能用心揣摩“上意”,将自己潜心修炼成一种“格式化”物种。即便是这样,这种“境界”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,非要在“伴君如伴虎”的恐惧之下,在长期侍奉领导和官场周旋的历练之中,经过用心的点点滴滴的不断积累,方能渐致“最佳境界”—由“有心”逐渐驯化为“习惯”,进而修炼成流淌在血液中的“官场本能”。